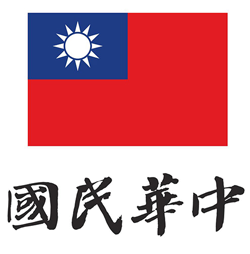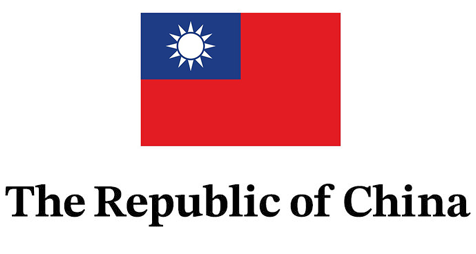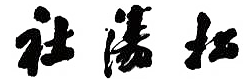Salvation and Martyrdom Exhibition
7 to 23 July the 10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2017)
Salvation and Martyrdom Exhibition 7th to 23rd July the 10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2017)
At 2pm on Friday 7 July in the 10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2017), the National Flag Allegiance Committee of Sung Tao Society held the Salvation and Martyrdom Exhibition at Ye Classical Art Gallery in Huashan 1914 Creative Park. The Exhibition was to commemorate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rco Polo Bridge Incident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n 7 July 1937, Japanese Army used the pretext of searching for lost soldier and demanded to enter the City of Wan-p’ing. The regimental commander Chi Hsing-wen (吉星文) refused and the Japanese attacked. Battle raged around the Marco Polo Bridge. On 17th May, Chairman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委員長) gave an address at Lu-shan. Some of his words are:
“If war is to break out, no matter whether you are from the south or from the north, no matter whether you are old or young, no matter who you are, you have a duty to defend national territory and fight against aggression. You have to be resolved to sacrifice everything.”
The whole of China was thus mobilized to fight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Eight years later China finally gained victory
The Salvation and Martyrdom Exhibition ended on 23rd July, and lasted a period of sixteen days. The exhibits included works by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a number of martyrs such as Ch’en San-li (陳三立), Wu P’ei-hu (吳佩孚), Tai-li (戴笠), Ch’en Pu-lei (陳布雷), Tai Ch’uan-hsien (戴傳賢) and Chi Hsing-wen (吉星文). Eighty two veteran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ere invited to write three mottos on cardboard panels which were also displayed. The mottos are:
“Long Live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g Live Free China”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Nation Building were Fought for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 exhibition catalogue was published with an article by Ms. Chang Hsiao-feng (張曉風女士). Mr. Eric Ye (葉一豐先生) of Ye Classical Art Gallery sponsored the venue. A number of exhibits were loaned by Mr. Wu Hui-k’ang (吳輝康先生) and Mr. Huang I-chen (黃議震先生).
Photo
https://www.rocours.com/index.php/events/item/244#sigProId37d40deac8
Venue
https://www.rocours.com/index.php/events/item/244#sigProIdfa06354071
Opening
https://www.rocours.com/index.php/events/item/244#sigProId70a6fb1288
Promotion
Preface by Soong Shu Kong
Preface by Soong Shu Kong
亭林嘗言:「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生于山嶽崩頹之際,其言慷慨淋漓。
吾世奚異?抗戰勝利,大難續繼,焚戮愈烈,國脈頓挫,而今滄海橫流,風雨如晦。救世君子,若大旱殷盼之雨露。古之仁人志士,有以生救國、保疆土、衛蒼生,成敗弗計;有以死殉國,壯青史,存道統,待百年後再興。千載以降,國有興衰,道統不絕,蓋救世君子以丹誠積瀘之氣節填海,以碧血凝固之死節補天而已。四方競拯天下,何患國之不興?
宋緒康謹識
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值七七抗戰八十週年
Foreword by Huang I-chen
Foreword by Huang I-chen
一八九四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自此開始了日本一再侵華的血淚史,自一八九五年台灣的割台抗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南京大屠弒……,無一不是血跡斑斑的一頁痛史。
從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五十一年間日本軍國主義鐵蹄蹂躪,苦海一片,多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骨肉分離?其中苦難豈是今日的我們所能想像?
張曉風教授為文〈寫給外公──兼懷上一代的英靈〉有言:「苦難未必只發生在中日戰爭啟端的一九三七那一年」,的確!歷史不能遺忘,經驗必須記取。
如今抗戰發生八十週年,老兵凋零,所剩無幾、中樞停辦紀念活動,所幸松濤社及許許多多有心人士,奮臂疾呼,否則這慷慨壯烈的抗戰史頁,恐怕都將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轉,湮滅、殆忘!
黃議震
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
Foreword by Chi Min-li
Foreword by Chi Min-li
父親成長的年代,正是國家處於內憂外患與動蕩波瀾的混亂時局,他在就讀師範時,鑒於國難當前,毅然投筆從戎,進入國軍部隊後,此時正是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及鯨吞東北之時,更是在華北步步進逼的危難關頭。父親在民國二十二年的長城戰役初露頭角,展現他不怕死亡的軍人氣節,由於此戰役的卓越表現,父親被拔擢為二一九團團長,接任宛平城的重要防務,肩負抵禦日軍與保衛國土的第一線任務。
盧溝橋在宛平縣境內,是座擁有七百多年歷史的石橋,該地為通往北平的交通要道。民國二十六七月七日深夜,日軍於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內搜查,結果遭到父親的嚴詞拒絕,雙方在交涉期間,日軍及對宛平縣城發起攻擊,父親率部奮起還擊,數次擊退來犯日軍。
八年抗戰期間,父親率部血戰於華北及華中各地,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並與日軍長期周旋,曾在徐州會戰掩護友軍撤退,並與張自忠將軍一同參加隨棗會戰等戰役,他在此期間曾多次因作戰而身受重傷。日後他曾對家人們說:「當年在華北親自上陣肉搏殺敵時,遭日寇武士刀削去肩頭負傷,始終不敢在自己的母親面前更衣,避免這個〈三指填不滿〉的傷口喚起母親的心痛。」,這是一個軍人在面對忠孝之間難以兩全的至高情懷的表露。
民國三十八年父親隨政府撤退至台灣,最後出任金防部副司令之職,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十八時三十分起,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砲擊,短短數小時內落彈五萬七千餘發,當時父親與另外兩位副司令趙家驤及章傑將軍遭遇砲擊,兩位副司令當場身亡,父親於八月二十四日為國捐軀,他為保衛國家堅守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軍人當馬革裏屍、戰死沙場,父親的一生幾乎都在戰場上度過,我相信父親應無愧於身為一個中華民國的軍人,也充份展現了軍人魂的信念。
吉民立
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
Article by Chang Hsiao-feng
Article by Chang Hsiao-feng
一、日本軍方,連狗都有一墓
外公!我親愛的外公!
在我有生之年,我從來不曾叫過你一聲外公,因為在我踏入這個人世之際,你已經離開這片大地兩年之久了。
那年轟炸,在桂林,民國二十八年一月春寒料峭,我們蔚藍色的領空遭到了強虜的姦污。桂林山多,也就有些山洞,你的責任是調度火車入山洞,以躲避日本軍方投擲的炸彈。那時你是鐵道運輸湘桂線區的軍職司令,而日本人轟炸桂林,也已炸了兩年了,並且是持續狂炸。那時,距離他們所說「三月亡華」的狂言,戰速已遠遠落後,仗已打了十九個月。中國,在積弱三百年之後,拿著大刀和頭顱跟他們的先進武器硬拚,居然也能讓他們知道,人類不是那麼可以輕易辱慢的!高貴的民族,不是供瘋狂的野心家來消滅來凌逼的。
火車順利入洞了,所有車廂和車上的人都安全了,天上的炸彈忽然以可咒詛的速度墜落炸開,外公,你自己反而走避不及,被氣流震飛遭撞,於是仆倒昏迷在地,從此沒有再站起來。
外公,你原是鄉間富紳,家有好幾間店面,又有良田千畝,本不必就任公職,但那時候,誰忍心讓大好江山淪於日本鬼子手中?你死那年,才四十八歲。(而我的母親,你所鍾愛的女兒,卻恰好活了你兩倍的年紀。)
我想到此事,不覺仍想嚎啕,仍想找一座荒山絕谷來痛哭、來揪髮、來裂眥、來泣血、來悲嘯撼山、來跺地震天。那是我母親終生的痛,也是我必須繼承的痛啊!
根據某些統計,中國軍民在那八年(或連東北地區,算十四年)死了三千五百萬人,如果我們以四億五千萬來算那時代的總人口,則每十三人中就有一人死於這場戰爭──這場打著「大東亞共榮」的謊言旗幟來進行其殘酷屠殺的戰爭。這種死亡比例,其實已是每一家族出一人頭,供日本軍國主義用來血祭其侵略之惡行。那時代,人人都有親戚直接或間接死於日軍之手。外公,要哭,那真是要「哭殺天下無眼睛」啊!
我有個記者朋友,去雲南拍滇緬戰爭的當年現場,在日軍埋骨的墳塚間,赫然發現一座軍犬的墓,他忍不住淚如雨下。啊!原來日本軍方連狗都有一墓。而我們的軍民,命如草芥,只有以肝腦塗地,以鮮血匯成長渠,在神州的膏土上縱走橫流,書寫那說不盡的哀恨──以無名氏的身分。
二、 第一個殉職的車站司令
六十年後,我陪母親到桂林要為你掃墓整墳,然而荒草斷碑,何處是你埋骨之處?母親唯一記得的資料是:「隔江面對著獨秀峰。」
碑沒了,只能告訴自己,一代英靈已化為泥壤,在陽朔的青山綠水間。
唉,外公,如果我們生在太平盛世,如果沒有那場可咒可詛神憎鬼厭的戰爭,如果你能牽著我的小手,跟我共話……
你生平最愛花錢、花力氣去搬運一些收藏品來放在家裡,那奇怪的收藏品是漢代的畫像塼。啊,若你能為我一一指點,那是何等幸福──你謝世之後,這些東西也都不知去向了,我認為是日本人偷走了。算了,偷幾塊畫像塼又有什麼,他們盜奪的是一代精英的身家性命啊!
曾經,屬於我的孩子的世界,在母親的刻意保護之下,竟不知有戰爭死亡和流血。我當然也躲過警報,蹲過防空洞,但全然沒有記憶,人世的苦難於我竟是諸邪不侵。我記得的只是抗戰勝利了,我們要坐船回南京了,而小販拿到船上來售賣的南豐橘子是多麼甜美薄皮且多汁如蜜泉啊!
而外公,你的事,是我讀中學時候才聽母親說起的。啊,原來我有這樣一位外公,原來他英年早逝,死在遙遠的離家千里的異鄉,且死於非命!悲傷啊,後來我讀你的記載,是在《靈壁風物志》上(1983 年出版,陳樹聲撰述,137 頁),文字只四行:
「謝幼支……因職責攸關,未能逃避,即被炸殉職,是為抗日戰爭中殉職之車站司令第一人(張午炎記述)。」
在戰爭的年代失去的美好的人、事、物,是永遠無法補回的,而我失去的,是我本該理直氣壯可以擁有的。世上任何一個小女孩,醜陋的、漂亮的、窮的、富的、愚笨的、聰明的,都有權坐在外公膝頭,抬起頭來,傾聽一則則古老的故事……。然而,有人把我的這份福祉生生奪走了。
三、 絕美之景 絕美之物 絕美之人
成年以後,我有機會多次去京都、奈良、東京、大阪等地一遊。在唐招提寺,看到鑑真和尚的真身。遙想一千兩百年前,此人眼已盲黑,身是殘年,猶在凶惡海象中踏上小船,遠赴日本去弘法渡人,曾受鑑真捨命以事奉的日本人啊,為何要濫殺鑑真大師的故人呢?
唐招提寺的粉色櫻花,郁郁紛紛,既強壯又盛美,開到爛漫無邊處,令人仰天欲淚。鑑真大師啊,鑑真大師啊,真想和你說說話啊,你不朽的肉身坐在此地千把年了,我遠來見你,想跟你敘敘舊,但說什麼呢?說愛?說恨?說和平?說戰爭?說「我執」?說死不知悔的惡欲?說我失去的一切?
詩仙堂中,四百年前的石川丈山繪製了三十六幅唐宋詩人,來虔誠供奉。唉,世上竟有這種人,奉異國詩人為仙客,並且傳其詩教!庭院中春天是杜鵑花,夏天是蒼松,秋天是楓紅,冬天是白雪。澄明的水沼中有鳶尾花、莎草和水鳥,竹門上則寫著「梅關」二字。「梅關」其實是粵北和江西的交界,六祖惠能和〈牡丹亭〉故事中的柳夢梅都曾走過此路。此地是山頭,在現代化的戰爭裡,從空中掃射而下特別方便,當時此地駐軍死傷無數,沒有一寸土不是飽含人血的。
在京都看到「梅關」題額,不免亦喜亦悲,喜的是千里同風,在異域也有「梅關」。悲的是,四百年前的石川丈山建詩仙堂之初,哪裡知道這「以梅為關」的美麗地點,竟是日後日人射殺漢人之處。
日本處處皆有絕美之景、絕美之物,乃至絕美之人,令我神迷意牽難以忘懷。但何以在戰場上殺心頓起時,中國人卻是他們覺得可殺可宰的畜生!
湯川秀樹,二戰後得物理諾貝爾獎,戰爭期間,不廢研究,值得欽敬。然他另一個身分卻是「漢詩迷」──我佩服他對漢詩的佩服。只是,物理學是天機欲洩的學問,漢詩則是直指天心的本然,這位坐擁兩項世間最珍貴學問的人,在戰爭期間曾對漢人幾遭滅種的大難有一絲絲傷惻嗎?
小林正樹,小津安二,都是多麼優秀的導演啊!
淵田美津雄,曾乘航母赴珍珠港主持轟炸大事的人,戰後歸鄉執鋤務農,靜思之餘成了基督徒,並且做了牧師。曾經也來過台灣,深悔前愆。我曾親聞其人證道,他還說了一般西方人不易破解的密碼,1941 年年底,那次不經宣戰的空中偷襲,之所以選擇「虎!虎!虎!」作行動代語,其實,是因為淵田自己本人屬虎的緣故。哎,淵田,淵田,雖然你已改邪歸正,但當年的你為什麼不想想,你屬虎,虎是十二生肖的思維,你既認同這生肖的美學,為什麼不能認同生肖所屬的中國的尊嚴呢?
永井隆,一個原已帶病的天主教的醫生,在長崎遭劫之後,勉力搶救傷患,直至油盡燈枯才溘然閉目。
以個人來講,日本的好人甚多。以物質而言,日本的工藝製作精美審慎。以風景而言,日本的景區清潔整齊,服務態度也恭敬誠正,且能體貼入微。大和民族實在是個優秀的民族啊!
四、「三月亡華」和「三天亡日」
要恨日本的庶民,實在恨不下去,但日本軍國主義還是該恨的!殺人、姦人、搶人、辱人、毀物(包括毀去商務印書館極珍重的書樓藏書……),而且至今死不認帳。
外公啊!我和一般慈眉善目的女子不同,我願上帝在這件事上不要賜我一絲半毫慈悲心。相反的,願祂賜給我多多多多的恨,因為恨也是一種能量,而這能量又常是極容易流失的。因為歲月湮遠消逝,因為現實生活瑣屑煩人,因為有人集體失憶。啊,上帝,讓我記得,讓我記得人類邪惡到極致時的樣貌,墮落到比魔還魔,比鬼更鬼時的嘴臉,以免地球上再發生一次拷貝翻版的戰爭。
曾有一則謠言說,投擲原子彈的美國軍人因自譴而精神崩潰進入瘋人院了。不對,那人丟得很痛快,他是為中國百姓丟的。原來,他的父母曾在山東宣教。他自小眼見日軍種種酷行劣跡,發誓要為中國人出一口氣,他丟下原子彈的時候,只說了一句:
「胖子,去吧!」
胖子是他給原子彈的暱稱,因為它的外型圓圓胖胖的。他丟彈的時候心中坦然。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戰爭的「挑釁者」,而是戰爭的終結者。
癡昧的天皇相信軍方的狂言,自以為用他們擁有的「高科技」,便可以「三月亡華」,不料三月亡不了中華,三十個月也不行,到了快一百個月的時候,日本上空出現了「超高科技」,日本於是自己亡了。國人認為天道一向厭惡「過盛」,「過盛」而又「凌人」,更是天道所忌,日本怎能不亡?
「三月亡華」不成,世人看到的是簡單利落的「二彈斃日」和「三天亡日」(兩彈各於1945年8月6 日和8月9 日投擲,相隔三天)。
不過,如果我有法術,讓我能穿越時空,把此刻的我填回當年1945 的身子裡,加上,如果我可以有資格去跟美國杜魯門總統對話,我會建議他不要擲原子彈,至少,花草、樹木、小狗、小貓是無辜的啊──
我會建議他讓戰爭繼續打下去,反正日本已敗象畢露,讓他們自己把自己的一口元氣耗盡,讓日本打到不剩一兵一卒(以他們的倔脾氣看,會的),只留一天皇,孤家寡人,坐在寶座上,自我切腹以謝社稷黎民。
日本童書作者佐野洋子曾在她最後一本書中提到她的堂姐佐野桃子,戰爭末期才十幾歲(洋子自己當時人在北京),卻不上課,學校成天派他們去掘松樹根,為什麼挖樹根呢?因為戰爭需要燃油,沒有油,仗打不下去,松樹根有一點點油,不搾可惜,所以那年代的日本少男少女皆須埋頭挖樹根。桃子堂姐雖只是十多歲的小女孩,也看出來了,日本必敗無疑。
原子彈給了他們下台階的機會,死要面子卻不顧是非的「日寇」自此裝可憐,邀同情,一裝裝了八十年。其實他們的「二彈之苦」也不過就是佛家常說的「因果律」罷了。頗信佛教的日本軍閥和人民怎麼忽然又不懂此律了!
日本至今不讓他們的學生知道這一段歷史,你若碰到日本青年不妨問問他們歐洲的戰爭,他們會顯得很有「國際觀」的樣子,說得一清二楚。但你若轉問他1937 到1945 之間的中日戰爭,他會眨著純潔的眼睛,說:
「咦?中日有打過仗嗎?」
啊!外公,外公,你早早走了,我軍花了八年時間,拚得個「一方慘勝,一方慘敗」,連人心人性都打涼了。財產沒了,生命沒了,文化削減了,家庭破碎了,黃金年華在逃難途中虛擲了……,付上那麼大的代價,如果有個日本人是條漢子(當然,女漢子也行),站出來說一句:
「我知錯了,請寬恕我。我保證以後的歷史中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了!」
那麼,這一切慘絕人寰的損失就算值得。
但不是,但不是,日本軍方沒說的話,我來替他們說了吧:
「嘿,嘿,我打你──不錯!我打了你,有本事,你回手呀!怎麼樣,你沒本事吧?所以,我就打你!射死你,打死你,殺死你,砸死你,燒死你,鋸死你,毒死你,溺死你,餓死你,凌遲死你,我愛怎麼弄你怎麼弄你,誰叫你弱!哼,別跟我講什麼公理正義,巴格亞鹿!(日語罵人的話,指「蠢豬」。)老子就打你!」
這是一個可愛可敬復可恨可鄙的族群啊!我不原諒他們,是因他們至今自認沒有什麼事情需要「被原諒」。
五、 那隻桃子和這隻橘子
外公,外公,我曾遺憾沒坐在你的膝頭,和你共吃一塊飴糖,並且聽你講故事。你好古,必有許多故事可講。但既然不行,我且反過來,講兩個故事給一百二十六歲的你聽吧:
從前有對老公公老婆婆,在河邊撿到一枚漂來的桃子,打開桃子,裡面蹦出個小男孩,因此取名為「桃太郎」。桃太郎一夕數變,不到一個禮拜就成年了。成年的桃太郎請老母親為他做了一堆黃米糰子,(外公,別插嘴,黃米是什麼米,我也不懂,或許是小米吧?)背著,便四處去招兵買馬起來。有黃米糰子作軍糧,他的背後遂跟著貓呀、狗呀、猴子呀……,他們的任務是什麼,是要去打一座島,名叫鬼島。(哎,哎,外公別問我,鬼該住在海島上嗎?我也不知道哩!我所知道的鬼都比較愛住在另一個地方──就是人類的心宮裡。哎,不說了,外公,讓我把故事講下去吧!)好,他們到了鬼島了,鬼王一聽說大軍壓境,便嚇得跑出來投降,(對,對,外公,別吵,鬼既不是血肉之軀,難道怕桃太郎來殺頭嗎?我也不知道桃太郎是憑什麼本事「三分鐘亡鬼島」的。)總之,鬼島之王,照桃太郎的吩咐把金銀珠寶都堆在桃太郎腳下,桃太郎於是包捲起珠寶,志得意滿,班師回朝了。那些貓、狗、猴子也都一起耀武揚威回到日本本島,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這個故事的教訓是什麼?哎,哎,外公你還真是個「老式的聽眾」,不過,好吧,你既然問,我也就說一說。第一,那位桃太郎是漂來的。第二,他很快就長大了。第三,他準備了一些軍糧,靠這些軍糧,他居然組成軍隊。第四,籌軍糧不易,搬運軍糧更不易,所以必須速戰速決,必須「三分鐘亡鬼島」。第五,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要先把對方醜化為「鬼」,「打鬼」是偉大的事業,所以,可以做。鬼王獻出珠寶,那更是天經地義。可是,到了二十世紀,桃太郎卻來打中國了。中日戰爭打了八年,軍備方面可不是靠幾隻黃米糰子就能解決的呢!)
好了,外公,以上是日本的桃太郎故事。接著,我再來講個橘叟的故事給你聽。在講之前,我先講一段楔子,我去年到成都演講,講完了,主辦黎先生帶我在附近逛逛,逛著逛著,他忽然說:「邛崍就在附近。」我一聽,大為振奮,立刻大叫說:「帶我去,帶我去,這是神話裡的地方呀,不料今天我們竟走到神話裡來了呀!」同行的人都不知我在講什麼,我一時也不想講古。其實,外公,我要跟你說的《玄怪錄》(或名《幽怪錄》)中的橘子故事,就發生在邛崍。那天我們真的到了邛崍,找到一家茶館兼書店的地方坐下,抬頭一看,後院裡還真有一棵橘子樹,樹上待採的橘子真有嬰兒頭那麼大。我十分驚奇,原來古人就算寫小說,背景道具也都能「有所本」。橘叟的故事,就是講兩隻大橘子的故事。外公,你懂文言,有些地方,我就直接唸給你聽吧!「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盡收,餘有兩大橘……,巴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鬢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
他們玩象棋是帶賭博的,但目的不是錢,而是些希奇古怪的東西,例如「瀛洲玉塵九斛」等,其中有位老叟說:「橘中之樂,跟我們從前在商山一樣樂(看來他們是商山四皓),但不得深根固蒂,總有討厭的笨蛋來摘我們!」另一個說:「我餓了。」就去袖中抽出一根長成飛龍形狀的草根,自顧自地吃起來。他削一片吃一片,草根居然又自動長回原狀。吃完了,他口中含水把草根一噴,草根立刻變成長長大大的夭矯飛龍,載著他們四個老叟,飛到不知何處去了。說故事的人說,相傳這是陳、隋年間的事,書寫者則是唐朝人,他把故事定位於一百五十年前。
唉,外公,你問我為什麼講這個故事,因為五千年來,國人羨慕的生命情境可能就是這樣的吧?活到老,有幾個知己朋友,把自己封在一團安全的小窩窩裡,依著棋盤的規矩,玩著天長地久的對奕遊戲,視富貴利祿如浮雲──這沒有什麼不好,如果全球的人皆如此和樂知足與人無爭,未嘗不是美滿世界──可是外公啊,世界如滾輪,容不得我們躲在芬芳馥郁的大橘子裡,人家要摘我們剖我們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辦呢?而外公啊,你我都知道,不是人人都能弄一隻飛龍來搭乘跑開的。
桃太郎太像日本人,橘叟太像我們自己國人。今後日本人要走什麼路線我們管不著,但我們自己呢?總要過些比「小確幸」更多一點的日子吧?苦難未必只發生在中日戰爭啟端的1937 那一年。
外公啊,陽朔山水中的外公啊,一生捐錢又捐軀的外公啊!你安息吧!
張曉風
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
Book
https://www.rocours.com/index.php/events/item/244#sigProId6bdb23746e
Vestige
https://www.rocours.com/index.php/events/item/244#sigProIdf70c20cfbe